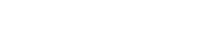带着诗心回草原

文章图片
图片发自App
我说:在草原的深处,天空中时常飞过一两只海鸥,这话多数人不信。类似的话说:沙漠里,有几只企鹅在踱步,好多人觉得更加匪夷所思,就像诗人的抽象或意识流。而实际上,在南美西海岸,阿塔卡玛沙漠延伸至海边,洪氏环企鹅就在沙漠里散步。它脖颈上白色的斑纹像戴着项圈,叫声诡异,像驴鸣。

文章图片
图片发自App
在故乡的草原,随便爬上一处高岗,就能眺望远处那个叫海的湖。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散落着几个小岛,像碧玉盘里放着几枚青螺,如果你心绪宁静,几乎可以听到岛上的喇嘛庙里袅袅的梵歌。湖叫青海湖,古称西海,湖里遍布鱼群,由此再解释海鸥何来何往,便都是赘述。知道有海鸥,可你未必知道湖边还有蜻蜓,有蜥蜴。经历过刻骨铭心得苦寒的人,往往很难把这温带的生命和雪域高原联系在一起。
人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是人太过渺小,像一只小蚂蚁趴在篮球上,眼前也是坦荡如砥的一马平川,就连我这样的原乡人也不敢说自己了解这片草原。所以,席慕容在《如歌的行板》中说: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不知道的,不然草木如何循序生长,而候鸟都能飞回故乡。
【带着诗心回草原】像我们一样,不甚明白的还有诗人西川。有一年,西川去青海湖旅游,按图索骥地找到一个叫哈尔盖的小站,觉得那里离湖很近。下了火车才发现,湖还很远。夜宿小站,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在高原看天,天很低,白天看着云彩低,是云傍马头生,晚上看着星星低,是手可摘星辰,于是西川在诗里写:在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胆子,但屏住呼吸。

文章图片
图片发自App
在草原浩瀚无垠的夜空下,会感慨自己得渺小,因为渺小,我们对无奈的现实和无法预知的未来,充满迷惘而又满怀期待。
也许就是缘份吧,假如西川再往前走一站,也是一个小站,在站台上就可以看到黛蓝的天空下,宝蓝色的湖,南风徐徐,吹来湖水的咸腥。小站叫刚察,是我草原上的家。
多少年,从懵懂少年到两鬓霜花,总是这样怀揣诗心,远眺故乡。以至于二十年后,坐在回乡的火车上,车轮在铁轨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时,都觉得是刚察,刚察,饱含着诗意的呼唤。

文章图片
图片发自App
站在草原上,你会问:铺天盖地的油菜花去哪了?金色的麦浪去哪了?我家的小屋去哪了?(所幸没有看着它地拆掉,乃至不会心碎)。你会发觉所谓“阔别”一词包涵着多么悠远的意境。我宁愿相信是这绿色的草,潮水般的冲击着小屋,年复一年,潮起潮落,小屋最终变成一片瓦砾的。退耕还草,草原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这让归乡的人不免心生凄凉。草是草原的过客,人也是,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永恒,即便故乡的记忆被自己无数次的回放,纵然历久弥新,仍旧不过是时间里的瞬间,是空间里的片段。
于是记忆变得弥足珍贵。回忆成为绵绵不绝的幸福。

文章图片
图片发自App
在冬天,我放着我的羊,草原一片焦黄。在离我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团色彩斑斓的东西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赶着羊群追赶,可它趁狂风逃逸,追啊,追啊,太阳落山了。追啊,追啊,星星挂满天。一截土墙挡住它的去路,走近才看清,那是一只破充气的塑料鸭子,红色的嘴,黄色的身体,一缕风蜗居在它的身体里,使它看起来依旧丰腴。我怀揣这只鸭子,心里满是欢喜,不因为它是只破鸭子。
长大后,我拿着画笔,时常会怀念那只鸭子。可以想像在冬天,无色的草原上,一只色彩鲜艳的鸭子给我心动神摇地感动——那年我十岁。
无端想起童年的片段,发现生活磨砺后的自己依旧抱持一份童心,痴心不改。有人质疑我画画,没有啥成就,我就说:我只想给自己一点颜色看看。有人喷我写作,闷骚的文艺中年,我也不着急,因为我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是写作给我寂寞的心灵最大的慰藉,她是我生命里最长情的告白。某一天,当我打开的不是金碧辉煌的殿堂,而是一道柴扉时,我心里依旧安详,因为我忘不了,在我童年时,在我拼命追赶到的,那只揣在怀里依旧满怀欣喜的破鸭子。
说点题外话:渥特.迪斯尼的小女儿从幼儿园回到家,毕恭毕敬地问父亲:请问,您是渥特.迪斯尼先生吗?
是的。
那么再请问是您创造了唐老鸭和米老鼠吗?
是的,孩子。
那么您好,渥特先生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文章图片
图片发自App
有一种晃悟充满了欣喜,相濡以沫的好多年,竟然是不明就里。当我知道仓央嘉措就是在这湖的北岸圆寂或者远遁时,我也像沃特.迪斯尼的女儿那样,对这个朝夕相处的草原顿生崇敬。这里因此成为诗意的天堂,乃至郁郁青草皆为般若,朵朵小花皆为法身,伏到在这草原上,我想对着天空问一问:请问是仓央嘉措尊者吗?请问是写世上安得双修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的诗人吗?
无言以对,只有风轻轻吹动发梢,似那位活佛诗人给我这生了白发,依旧有颗童心的人智慧的抚顶。
2017/5/26大漠
推荐阅读
- 闺蜜,太甜蜜的词会带着刺
- [个案学习070]|[个案学习070] 一个带着童年创伤的个案如何推进
- 草原之旅——第一天承德僧冠峰
- 这是个带着有色眼镜的社会
- 期待你的成长
- 梦和远方
- 手写我心day12
- 带着爸妈儿子游广州
- 带着觉知生活,人生才开始变得有深度|带着觉知生活,人生才开始变得有深度 快乐密码空间
- 让人无言以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