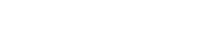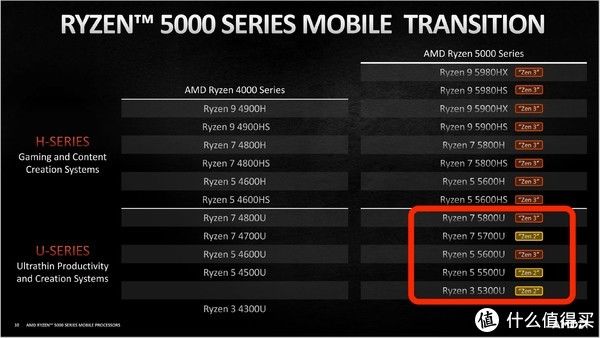第一千三百四十七天
我可用劲的对着来检查我的医生眨了眨眼。
这个努力从去年的冬天我就开始尝试了,每天都在试,每天都试好多次,没一次成功过,不过今天很意外,从那个医生的表情和招呼其他人的声调来看,他很明显的看到了我眨眼睛的动作。
要是早知道把安全帽从头上拿下来的那一下,竟然让我在医院里像死了一样躺了好几年,我绝对不会在防坠物兜网的底下站那么久,还把安全帽摘了。
那天的太阳和今天一样好,收工的时候,路过卷扬机,正好有一大片火红的彩霞在我们正在盖的大楼后面,鲜艳的让人讲不出话,工友们路过的时候都停下来看,我也是一样。说起来也是很奇怪,晚霞这样离得这么远的东西,只要天气不下雨,我们就能看见,可是在河南老家的娘和媳妇儿,还有闺女二妮,一年到头都见不着,只能是过年见上个几天,多亏现在有个手机了,有啥事儿也能打个电话......就这么想着,我顺手就把安全帽拿下来了,突然觉得啥东西就掉到头上了,低头一看,是半块砖头从兜网里掉出来了,一下砸到我了,再一抬头,就听见脑子里有个东西大声叫唤了一声,眼前的整个天全是晚霞,火红大亮,然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醒过来已经是在医院里了。眼睛闭不上,咋使劲也闭不上。我想说话,可是嗓子和舌头就像被关上了,两根管子从鼻子里头插进去,有一个出来的肯定是空气,有点甜,有点儿凉快。我想把头扭一扭,可发现不单是头和脖子,连眼珠子都动不了了,我一下害怕了,想,可能我是瘫了,让半块砖砸到头上砸瘫了。把我吓得心跳的咚咚咚,旁边儿有个啥机器,电影里头经常演的有,你心跳的越快,它就也跟着可快的叫,和工地上升降电梯超员以后嘀嘀的声调一样。医生和护士听到这声音了都来了,我就听一个医生说,9床有复苏迹象,边说边拿了个手电照我的眼睛,光很亮,像中午的太阳一样。可他左右都看了一下,然后说,没有明显反应,否认复苏,我想把手抬起来,或者是用脚把啥踢倒,让他们看看我现在就是光不能说话,已经醒了呀。可是和脖子和眼珠子一样,我的手我的脚,我浑身都不能动了,都不听指挥了。
再知道植物人这个专业词,是四天以后。
我娘,我媳妇跟着医生后头进来,三哥也来了。他们肯定是刚下火车,带着包袱。娘又老了一大块,我媳妇儿二妮她妈也是看上去很劳累,脸色很惨白,三哥也是,开始花白的头发都炸起来了,乱糟糟的。医生和三哥说我已经是植物人了,当时我娘,我媳妇儿一下就瘫坐到地上了,开始哭了,可又不敢大声哭,那压在嗓子里头可憋屈可憋屈的声音把我听得跟着也哭了,可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下来,啥表情也做不出来。
三哥听医生这么说,也哭了,转过脸看着我,然后和医生说,大夫,你看他咋能是植物人呀,他壮得和牛一样,啥病都不得,咋被砖砸了一下就成植物人了呀,你看他的眼睛都睁着呀......医生也走到我面前,拿出来那个手电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说,是睁着,可是你看他眼睛会动吗?脑外伤造成的植物人康复的可能性很低,你们家属得有个思想准备,后期的花费啊什么的得先有个打算......我听得很仔细,心想,这下可真完蛋了,大夫都这么说了,那这病看来是治不好了,大城市里人说话都有分寸,让有打算,看来钱是少花不了了。我使劲想说出话来,哪怕就发出一点儿声音也好,结果啥声音都发不出来,三哥就坐在我病床旁边,两只眼睛盯住我,可使劲的看我的眼睛,一会儿他眼泪流了一脸。我这心里就像刀子割一样,只想求老天爷就让我说一句话,要是真治不好就不要治了,把钱给爹娘防老用,给娃攒住上学用,花到这地方弄啥呀,可是老天爷一个字儿都没让我说出来,我眼前看着是三哥哭,耳朵里听着是娘和媳妇哭,心里头,是自己在哭。
大家都哭累的时候,大夫早已经出去了。三哥和娘和二妮她妈商量着咋去找工地的要医药费,三哥说,估计很不容易要到,得有几手准备,娘说,一定得要着,然后转过脸来看着我,又哭起来,二妮她妈就坐在我身边,双眼失神,半天没说话,忽然盯住我的眼睛,冒出一句,要是他们不给医药费,我也就不活了,死给他们看。我听到她说这个话,急的想伸手去拉住她,可是整个人一点儿啥动作都做不出来,就像被混凝土浇住了一样。
我就像棵树,躺在医院的被子里,眼睛闭不上,眼珠子不能动,也不流眼泪,每过上一会儿,就有个护士来给我滴眼药水,这个药水很稠,滴到眼睛里整个眼前的天花板就变形了,每次这护士来滴眼药水的时候,我都可使劲的想把眼睛闭上,或者想赶紧陪个笑脸,把手脚抬起来让人家看一下,可是全都办不到,没有办法吃东西喝水,整个嘴和舌头僵的跟铁铸的一样,旁边吊针架子上吊的大玻璃瓶子,只能用眼角瞄到一个边,里面是啥我也不知道,吊针戳在胳膊上,不很疼,不过非常凉,我就躺着动弹不了,喊叫不出来,哭不出来,我知道,自己真的变成一棵等死的人形枯树了。
要不是二妮她妈和我娘两个人,站到还没封上顶的工地大楼上要往下跳,医药费肯定是没有了。
她们两个人还有三哥,去和包工头要医药费,是因为医院催着让把我运回家去,说是这个病吧也没啥好办法治,要是没有医药费了,医院也没办法免费给治下去,只能转到其他地方或者回家。我知道,人家没有说出来的话,肯定就是我这个样子,治也没啥希望,家里又穷,能回去等死了埋到老家也好。娘一听就哭开了,二妮她妈当时就跪在地上给医生又磕头又哭,我看不着,只能听见水泥地板上磕头磕的咚咚响,然后娘也跪下了,也是哭着给医生磕头,两个人都不敢大声哭,声音憋屈的呀,就跟腊月里杀鸡的时候,临死的鸡发出来的声音一样,三哥最后也是跪下了,也是可小声可小声的嘶哑的哭着求医生。我的眼睛一点儿也不能转动,只能盯住那一小块白漆的天花板,他们哭的声音,一下一下戳到我的身上,我就想,老天爷啊,你为啥当时不让我被那个砖头一下就砸死算了,为啥要让我的亲人们跟着受这么大的折磨呀!
有了医药费,三哥带着娘回老家去了。
临走,三哥站在床边,身上背着当兵转业时候发的帆布包,娘坐在床边摸住我的头,就像小时候一样,哭着说,儿呀,娘知道你肯定能听见,你可千万要醒过来呀,等你醒了咱都回家,再都不到这地方来了,我可以肯定我也哭了,可是眼睛和脸就像不是我自己的,啥动作都做不出来,我知道,三哥走的时候肯定站在门口把我盯了一会儿,他当年当兵走的时候也是站在屋门口回过头来看了看我,那个要上战场一样的样子,我知道,虽然门口那个位置我根本看不着。
二妮她妈留在医院里陪着我。白天就坐在病床上,晚上在我的床底下水泥地上打个地铺,这也是和医生好说歹说了很长时间人家才勉强同意的。
这个城市啥东西都贵,从工地包工头要过来的医药费每天要给我用。我现在都不用自己解手了,有个尿管子连在我的身体里,一天到晚挂了一袋子尿在身边。二妮她妈想尽了办法去弄钱,先是把旁边儿的一个病人的护工兼职了,又去帮护士打扫卫生挣钱,我就躺着,眼睛每天被眼药水泡着,耳朵听着身边发生的事情,清清楚楚,可是无能为力,为了省钱,二妮她妈成了半个护士,滴眼药,擦洗,都成了她的事情,有时候我就像个木头家具被她翻过来再调过去,只是为了防止我躺久了生褥疮。
她经常跟我说话,家长里短,开始还偶然能笑一笑,后来时间长了,渐渐地也开始不说话了,也不笑了,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任谁,成天看见一个像我这样的和木头一样的残疾,也就不愿说话了。
有一天,她从早上出去,过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回来。
可能出去的时候已经和护士打过招呼了,那一天所有的活都是护士做的,我着急也就是干着急,啥也干不了,就只能躺着,盯住天花板,数数,想了好多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酸甜苦辣,自己在心里头一会儿哭,一会儿睡,一会儿醒,熬了一天。
到了病房快关灯的时候,二妮她妈回来了。一声不吭的在地上铺铺盖。天全黑了以后,她就坐在我身边,两个手抱住我的脸,我知道她哭了,眼泪掉在我的脸上冰凉冰凉的,她和我说,建国,我知道你能听着,实在没有钱了,医药费前天都不够了,我再去找工头人家说干脆都没有钱,让咱到法院告他们,我说,那俺男人的病咋办呀,工头说,那他管不了,说你自己在工地不戴安全帽是违法的,我就跪下求他,人家把我撇下跑了,我实在没办法,又跑去求人家,让人家把我留在工地上看有啥活干没有,说能做上个饭,我就每天过去一两个小时做饭,你看中不中?
我又能有啥表示呢?整个身体都已经不是我的了,眼睛只能直勾勾的盯住一个地方,二妮她妈把我的头抱起来,正好面对着窗户,外头黑得很,我啥也看不清楚。
时间,现在对我来说也没啥意义了。我的每天只是从天花板上的那一块地方忽然变亮开始,然后看着一点儿一点儿的再变黑。点眼药,翻身,擦洗,换吊瓶,听那些医生护士说话,听着旁边床位上的老干部家里人像新闻里头领导干部慰问家属一样来看他,老头子比我进来的时间长,也是植物人,不过我想他肯定也醒了,肯定也和我一样。我觉得我被判刑了,被半块砖头判了个无期,监狱也小得很,就是我自己的身体。还不如那些犯了罪的人,他们每天都还有一会儿放风的时候,可我,连这也没有。
慢慢的,连我自己都觉得变成一个木头也不是啥坏事儿了,等到哪天真死了,就刑满出狱了。
要是没记错,那天晚上应该是个十五,月亮光很亮,映到天花板上了。
二妮她妈一回来,就用一个手摸我的脸,她肯定碰上啥事情了,手抖得厉害,一会儿她又把我的头抱起来搂在怀里,她浑身都哆嗦了,我看不清能感觉得到,她哭得满脸都是泪,都淌到我的头上了,她嘴里一直可小声地说,建国,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等你一醒了咱俩就去离婚,我实在对不起你呀,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呀,工地上那个伙房不让我去了呀,你的医药费啥着落也没了呀,我咋办呀,后来听人说的在别的工地上女的可以跟工人睡觉挣钱,我就......我就......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就是个不要脸的女人呀,她说着,两个手捂了脸和嘴,呜呜的哭,我被她放开的身体很僵硬的斜到一边,脸正好面对着她,月亮光照过来,我看见二妮她妈的头发都是胡乱扎起来的,捂住脸的手上都是糙皮,我听见自己身体里轰的一声有个东西塌下去了,我还活啥呀!把自己老婆逼到了去卖自己给我看病这个地步,还活啥!还有啥脸再活下去!老天爷呀,你赶紧让我死了吧!我用了全身的劲,扯了喉咙大声哭起来,想把自己一下翻到地上去摔死到地上,可是我的身体,我的声音,我的眼睛,都像没有听见一样,很安静,一动不动。
天热起来了,二妮放了暑假和我三哥一起坐火车来了。
二妮看到我,我也看到了二妮。
闺女长大了,比我去年过年回去的时候长高了,头发漆黑,眼睛又大又亮。
刚看见我,二妮的眼神里头都是惊慌,可一会儿,她就把我的脸抱住,大声哭着跟我说,爸呀,你咋了呀爸,你赶紧跟我说话呀,你咋不说话呀,我是二妮呀,我和三伯一起来看你了呀,三伯说了,我一来看你你肯定就醒了呀......忽然又像想起啥事儿,跳下病床,跑到行李里翻出来一张纸,捧到我的眼前,哭着,硬挤着笑容跟我说,爸呀,你看啊,我考试都考的可好了呀,你赶紧说话表扬我一句呀爸爸,
那个纸是个成绩单子,上头写的二妮的大名,李慧,四年级期末考试数学语文两个满分,闺女啊,爸咋能不想和你说话呀,可是我讲不出来呀,以前商量到大城市来看看,不是像现在这样来看看呀,我对不起你呀,我的好闺女,你才是个小学生,咋能让你这么难受啊,
【第一千三百四十七天】二妮抱住我的头,她妈抱住她,两个人放声大哭,三哥站在病床旁边,表情麻木,可也是一脸的眼泪。医生护士来了,肯定以为是我已经死了,拿个手电把我眼睛照了半天,回过头来非常严厉地说,在医院不能大声喧哗,也要替别的病人着想,那医生的表情我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了,那是一种嫌弃到骨子里的表情,二妮到底还太小,当时止住了哭,可还是一下一下的抽气,小手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一直都不松开,就和每一次我过完年要重新回工地的时候,她在家门口送我也是一直攥住我的手不放,一样啊,我心疼的呀,闺女才这么小,我咋摊上个这事情,这要是有个几年都躺着,闺女咋办?媳妇咋办?娘咋办?谁去养活他们呀,三哥比我大了十一岁,眼看也老了,将来咋办呀?
我一定得活下去,一定得赶紧让浑身,都醒过来。
我最后一次看见病床头上的小纸片,
上头写的是:
床号9,姓名李建国,脑外伤无意识昏迷1347天,2014.5.18号意识恢复。
推荐阅读
- 即将到手三百万
- 第四十三篇接纳孩子的感受
- 亲子日记第三百四十二篇|亲子日记第三百四十二篇 暴雨
- 我的六合微生活(四十二)也说“体心胆”合练
- 《宋词三百首》75
- 亲情账户开通第一百四十三天
- 第13次三百分。保龄生涯之(50)
- 《精进》读书笔记(四十八)
- 写给四十岁的自己之一
- 珍惜当下(三百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