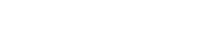那年端午
我被重男轻女这个思想伤害过吗?似乎是没有。因为回忆起童年,我没有什么悲伤可忆。可论上斤数二字,一个扁担挑俩娃,男孩终究是要重一些的,这重谁轻谁的话,理论上也成立。
儿时的春节总是更有年味,在没有朋友圈的那几年,靠煤烧热的热炕头有趣、手持烟花有趣、有本山大叔的联欢晚会有趣,连我们几个孩子的红袜子,看着都有趣,二叔是我们的大主厨,而半夜那顿饺子实行全民参与制,为了我们开心,家长们包的硬币务必让每个孩子都吃到,可算是想遍了法子,大人们吃到硬币不是藏起来就是举起来显摆逗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爷爷吃到硬币向来严肃的从嘴里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推,不藏也不张扬,这就更急得我们吃撑也要再来一个,那时候,我们很容易获得希望,也很快忘记失望。
小孩子口无遮拦,提起年夜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子(小弟)喜欢吃菜花,仁迪(大弟)最爱熘肥肠,在那些个什么要求都被爸妈满足的日子里,这成了我的不甘,后来回想这事,估计是因为我什么都爱吃,所以没人给我准备“专属菜”吧(自我安慰第一名)。也就是这种小确丧的存在,有次吃过年夜饭,我看着爷爷抱着弟弟,再想想我爷爷从来不主动抱我,加上没有“专属菜”,我越想越气。
“爷爷,你抱抱我吧?”我像宣战似的张开嘴。
【那年端午】“过来吧。”我爷爷饶有兴趣地把弟弟放在炕上然后向我伸出双手。
当时虽然电视有声音,奈何孩子声音也不小,家人都向这爷孙俩看过来。
“爷爷,我看你也不重男轻女呀?”我窝在他的怀里满意地说道。
我爸是家里老大,我出生时是我们这辈第一个孩子,我妈说我爷当时更希望我是男孩,后来我妈笑着说起这事,我推测当时她的脸能煎鸡蛋,那会若不是听我妈平日抱怨过几句,一个孩子也说不出重男轻女这成语来,我妈感叹:“你真是能卖我啊”。
我爷爷嗓门大的惊人,任谁循声都知道他在哪里下棋,王熙凤那出场词用在我爷爷身上都不为过,每次听杰伦的《将军》我都想起我爷爷。
有一次爸妈不在家几天,偏偏赶在这个时段我发高烧,我爷来家里啊接我去医院打针,那是我把他支使的最多的一次,是个麻烦的孙女,我让他给我买馒头,还要热的,买回来以后我垫在脉搏那里,满足的看着我爷,把剩下来的那个递给他,我爷说我以为你要吃,然后张了张嘴没说啥,我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觉得病好了一半,那会我也是淘气,是真淘气。
端午节,采艾蒿,我爷每年都去,我好奇,要跟着,那会的我,考试睡觉,上厕所睡觉,走路睡觉,一度被以为有血稠的毛病,却还是拱了起来找我爷一起上山,三点多啊,我的天,我的天都还没有亮。
我爷拿出我弟的黑皮靴子让我穿上,一路无声跟随,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次,忽然走到一片对我来说很高的植物处,我爷没避开不说,还让我跟着往里面走,我惺忪着眼睛看着我爷张开双臂,掠了一把周围的那些“高高的绿植”,然后往脸上一抹,我爷让我跟他学,我迟疑着学了一把,那是我第一次用露水洗脸,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大步跟上去边走边玩,笑的像田里的鸭子,咯咯不停。我爷爷个子高,我跟在身后,阳光从他的肩上一下下闪向我。就像那光一样,有些亲人没有无时无刻爱你,可每次照过来都像身边的露珠一样亮晶晶。
时间像脱了枪膛的子弹,转眼间爷爷被诊断为胃癌,家人倍感焦灼,幸运的是爷爷心态好,虽说没办法痊愈,可也比医生给出的预计存活时间要久,并且最后那几年他生活的也算是病人里痛苦少些的。爷爷临终之际,我在读大学,晚课刚上完还没有吃饭,叉着腰和大家讨论要去食堂还是订外卖的时候接到电话:“你爷要不行了,姑娘别着急,现在看一眼票吧。”电话那头我妈说。然后我订到离挂电话时间最近的一张硬座,瞪了一夜眼睛,时不时哭一哭,对面大哥俩个胳膊交叉在一块睡,中间想换个姿势,看我满脸眼泪吓得瞪圆了眼顿失困意,对我好一通安慰,到下车他都没再睡。我哥来接我,没去医院,我才知道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爷已经走了。后来我爸对我说:“爸没有爸了”。
我爷爷变成星星了,和那年的露珠一样闪,2019年的清明节假期马上结束了,时隔多年,您棋技肯定长了不少吧。
推荐阅读
- 我要做大厨
- 一个小故事,我的思考。
- 家乡的那条小河
- 第三节|第三节 快乐和幸福(12)
- 这辈子我们都不要再联系了
- 死结。
- 跌跌撞撞奔向你|跌跌撞撞奔向你 第四章(你补英语,我补物理)
- 我从来不做坏事
- 喂,你结婚我给你随了个红包
- 祖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