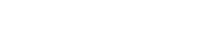道上闲言(十八)孔子与超人

文章图片
《孔子与超人》----作者:李率 己亥年 四月廿八 孔子反对极端。这并不是说,孔子不能随着性子来,事实上在有记载的文字中我们也能识别出孔子随性的一面,但那大都是在丧礼当中。
《论语·先进》中记载:“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颜渊死了,孔子随性了一回。“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摘自《礼记·檀弓上》)按礼说老师哭学生应该在寝门之外,孔子哭子路于中庭,表明亲近死者。
子路死,孔子又小小的随性了一回。我们当然不能残忍的说孔子违礼,作为今天人也没有这个资格。我们只是稍微的说能让孔子随性的人,确实不多见呢。
一个是孔子理智,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孔子是当时礼的专家,有着表率,与典范的作用;这点,我相信他自己也是非常清楚地。
但清楚,还要这么做,这就说明他真的想这么做,由内而外的,难以自抑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想要这样做,那就做呗,想哭个痛快,就哭个痛快,想在哪儿哭就在哪儿哭,这个时候谁也拦不住,这个时候理智完全无法战胜情感,因为太难过了实在是,所以人世间的特点在这一刻全都体现的淋漓尽致,酣畅的,痛快的让孔子知道了什么叫做:人间正道是沧桑。
同样遇到这事儿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乔达摩·悉达多,也是后来的释迦摩尼佛祖,佛祖在当王子的时候,据说也是因为亲眼见到了世间的生,老,病,死,以及饿殍遍地后,决心彻底的救人类出苦海,于是才在菩提树下专修成佛,就是后来的释迦摩尼。
王子也随着性子,去找寻真正的理智,去超越了。
这种,随着性子去放纵自己的情感,任其流淌,放任,对于,年轻人来说不难,甚至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的话,也能做到。
就像打滑梯,放任是最容易的,同时那个过程亦也足够酣畅了。就像“子哭之恸”一样,我们相信孔子是真的想这么去做,要打滑梯,情绪要爆发出来,学过《论语》,或者说读过《四书》,《五经》的人都知道,孔子非常欣赏颜回,甚至在说到某一点时发出了:“惟我与尔有是夫!”(摘自《论语·述而》)的感叹,这在《论语》当中几乎是罕见的。
“惟我与尔有是夫”是什么意思啊,是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这样的意思,任何人都知道这已经是把颜回“拔高”到和自己平齐的态度,所以颜子也被后世称为:复圣,足见颜回在孔门中地位之高不亚于孔子,(几乎)与孔子平。
但是颜回跟孔子走的,不完全是一个路子,颜回大概是儒门中的“无为”一派,有点儿类似于后来的道家;但也不全是道家,他还是儒。如果说,把礼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姑且可以分为四种人,而不是三种。
他们分别是:欲达(既:过),中庸,不及,以及超越。其中,像颜子,与释迦摩尼这种类型的,都属于超越型的人才,或者简称:超人。
怎么定义超人呢,用孔子的话说,就叫:“加于人一等矣。”(摘自《礼记·檀弓上》)这个加于人一等矣,就是超人。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礼记·檀弓上》同样有这样的记载,“孟献子禫,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禫祭,是在大祥以后的一个月,也即是二十七月而举行的祭祀,禫祭以后,孝子的生活基本归于正常,也即是说,可以唱歌儿,也可以唱的好听了。
然而实际上,理论上来说孝子在大祥除服祭以后就可以碰音乐,大祥是丧后二十五个月之祭,可因为还有个二十七月之祭,既:禫祭,故孝子在大祥以后碰音乐不能显示出太熟练,或太动听,这里面儿的原理就是:过犹不及。
以礼为标准的话,大祥以后理论上来说,可以碰音乐。但是大祥除服当天就碰音乐的话,这难免犯了有点儿过头儿的毛病,既我所说的:过了。你跟礼的标准一模一样,没人会说你错,但是你的这种“绝对正确”的行为,又显得有点儿不近乎人情事理了。所以孔子怎么做呢,《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孔子在大祥除服祭以后至少五天,他才敢碰音乐;要知道孔子是比较喜欢音乐的。这么喜欢音乐的孔子,他还等了五天,且五天时候还:“不成声”,就是不敢弹的太好,注意我的措辞,是不敢弹的太好,而非不能。起码我认为,孔子是能弹好的。
“十日而成笙歌”,十天以后,就能很和谐了。因为这是礼的规定,礼规定了大祥之后理论上来说,可以碰音乐的。这个时候,如果孔子迟迟不动(音乐),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那是孔子不及,或超越了。既:没有达到礼所规定的规范要求,或超越了礼所规定的规范,与要求。
而,孔子若太和要求、标准对齐了,既:“朝祥而莫歌”(摘自《礼记·檀弓上》)又显得有点儿过分了。所以十天,既不过分,也不会犯达不到的毛病,更不会超越。不早不晚,这就叫:中庸了。超人是怎么回事儿呢,超人是“存天理而灭人欲”,以礼来说的话,首先他定不会二十五月除服祭(既:大祥)就弹唱歌舞,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他也不会像孔子一样,大祥后十天,就可以:“成笙歌”。更不会像子夏那样“丧其子而丧其明”(摘自《礼记·檀弓上》)为儿子死而哭瞎了眼睛。
超人是什么呢,首先他不会被感情所累,孟献子的:“县而不乐”,与子夏的:“予之琴,和之不和,弹之而不成声。”(摘自《礼记·檀弓上》)不是一个层次的。因为子夏由于其性格等原因,大概是真的弹不好。
但是孟献子是可以弹好,却不弹。这跟我没有,或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与我有能力而不做,是同样的两码事儿。不做的人,并非不能做,或做不好,像子夏那样被情所困,或子张那样过于追求规则,追求完美,以至于像曾子所说的:“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摘自《论语·子张》)都不会,他更不会像孔子那样,“十日而成笙歌”,既,我折中。既不追求绝对的规则,与理智,又不会为情所困,也不会折中,这就是超人,为了更高的目标,可以存天理而灭人欲,这就是超人了。其有点儿像孔子所讲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摘自《论语·季氏》)道理,是一样的。
为了道,而灭人欲,这就是超人的目标。孔子,因为其所处时代,及其特殊身份等原因,不能这么做。但不代表孔子不想成为超人,或能力不足而成不了超人。不是的。
【道上闲言(十八)孔子与超人】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摘自《论语·雍也》)以及,释迦摩尼的化缘,苦行、孟献子的“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摘自《礼记·檀弓上》)等等,这些都会是孔子所褒奖的对象。因为,他们都属于超人的行为。道理,是一样的。----文作者:李率 己亥年 四月廿八 于自家中
推荐阅读
- 第二十八封信
- 未来丛林历险记
- 暴君公司|暴君公司 第十八章 做会员吗
- 2018继续以十八岁的心态活着
- 魔灵末路?第二十八章
- 给史多多的第一百五十八封信
- 八千里路云和月(九)究竟十八年前是谁邮寄的明信片
- 《精进》读书笔记(四十八)
- 第三十八章(最终章(一))
- 第三十八章|第三十八章 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