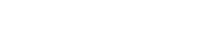壹
阳光真好!
阳光透过我身后的玻璃窗落下来,温柔地包着我。桌上落了一层细细的灰,本来那层灰是不起眼的,阳光一衬,细尘粒粒分明。抽张纸,水杯一斜,几滴温吞吞的水落在纸上,慢慢洇开。不急,慢慢擦拭。桌面、显示器、键盘、音箱、打印机,还有靠墙的那面的书、本子、笔、墨水、印油、夹子……一样一样,捡开来,擦拭干净了,又一样一样叠放整齐,再放回去。
擦干净了,再放回去也是要落尘的。人一辈子都在做着这样的无用功,就像吃饱了饭不能永远饱,总要饿,又总要再吃饭一样,虽是无用,却不可废止。世间难有一劳永逸的事,而人也总在无用里消磨。可是,若抽掉这些无用功,人还剩什么呢? 我乐意这样消磨自己。
【土豆】贰
阳光里,我在想那片青油油的土豆坡。
昨日遇见安子。安子串门,在飞哥的院子里。安子说他种过土豆,一两亩壮阔的山地,全部种土豆,到开花的时候,青油油的叶子间点缀着白色紫色的碎花,非常亮眼,如果你有幸走在地埂上,你还能闻到独特的清香味儿,不浓重,但足以勾引到许多小蜜蜂在花间闷头苦干,腿肚子上都裹满花蜜。
安子说话的时候,斜着眼睛看我,他一定觉得那壮阔的山地是我没见过的,而且那土豆花和花间腿肚子上裹满花蜜的蜜蜂一定能吸引我。事实上确实吸引了我,可当时我脑子里却出现了另一个场景:一男孩捉住女孩子的手,煞有介事地在女孩子的手心里写下一“冒”字,说,要记住了,这“冒”字上头不是“日”,也不是“曰”,而是下口框里一个“二”字。我忍也忍不住,就想笑。
我的笑让安子觉得很没意思,害得他再不想说话。
我也是种过土豆的。小时候母亲给了我一畦地,约十平米,就在屋后,我种的就是土豆。锄地,选种,挖坑,掩土,施肥,我自主操作,父母把地给了我,就由着我发挥。记得种那畦地,我很是上心,每天放学,都要去地边看看的,或者浇粪,或者除草,或者什么也不干,就在地边坐坐。我种土豆,有点像郭橐驼种树,旦视暮抚,已去而复顾。可能太勤勉,我的土豆结得并不好,枝叶茂盛,土豆寥寥。之后再没种过土豆,可那白的紫的土豆花和那清清淡淡的香却深深印在心里。现在,那青油油的叶子间点缀的白的紫的碎花就开在我眼前,一闭眼,就闻到香,仿佛就坐在母亲给我的那畦地边。
其实,安子不是想给我说土豆,他是想说,土豆的根不止往深处扎,还往远处播撒,土豆不是在正下方找到唯一的自己,而是在周围,在想不到的远方找到好多个自己。
我记不住安子说的远方和远方的自己,我只记住了安子说的土豆花。我在努力回想土豆开花的时节,努力想像那个在一两亩多壮阔的土豆花叶间走动的少年……像在看一部老式的电影,那老式的配音和老式的影像总让我回到过去。
我想,那些落入时间深处的我和我们,都是在远方了吧?
叁
冥想让人快乐。敲到这儿,日脚已经挪得更深,我的办公室几乎被晒透。窗台上滴水观音和吊兰的影子被拉得老长,从地上一直铺到进门的那张藤椅上。这变化缓慢而坚定,不受干扰。
一天已消耗了大半,之后,我要去政府取一份文件,回来取一份学校的快递,然后回家,做饭,吃饭,散步,看正在装修的房子,再回家就是画画,翻书,听电视……
日子就是这样的。最近有一项音乐教师的培训,巍哥问我去不。我直接推了。不去,我没想要把自己变成优秀的音乐教师,我就想这么由着性子懒散着,把无波无澜的日子折出无数的小弯弯,再把自己藏进去,偷闲,偷乐。